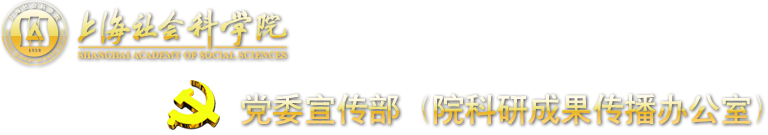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显示:中国第一个带有社会交往和共同生活性质的社区产生在西安的近郊半坡遗址区域内;上海第一个超越简单村落而拥有共同精神层面社会活动的社区则在如今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区域内。无论是中国还是上海的第一个社区,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也就是从那时起,社区广场(现在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活动时,人们总是要围着篝火(现在是聚焦灯光)唱唱跳跳。
令我惊奇的是,传统的庆祝习惯一直延绵到今天。我区现有的十三个街镇加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各类节庆期间举办纪念活动时也基本上以“唱唱跳跳”为主。我经常受邀出席,发现观众也经常是同一批人——分管区领导、东道主主要领导、各街镇分管领导和科室负责人、相关委办局分管领导和科室负责人;表演者往往也是熟面孔,因为社团化的群众文艺骨干实在是太需要表演舞台了;而媒体前来报道的记者因为“条线分工”之故,也是同一批人,新闻稿则是事先拟就的统发稿。所以,人们对社区文化的印象自然就是“唱唱跳跳”加“夕阳红”。
也许这是一种本性,或者叫做“与生俱来”;但我更欣赏“适当扬弃”和与时具进。因为十三个街镇加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在“某某节”一段密集的时间段里,最容易搞笑的就是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雷同化。本来嘛,一群中老年妇女穿着旗袍、打着花伞,在轻音乐中漫步舞台或公园绿地,还是很有美感的。但是,如果每一个街镇都是这个保留节目,而受众又是同一批人,感觉究竟会是如何呢?依我看来只能是倒胃口,因为“艺术变成了机械”、“美感变成了肉感”!
那么,如何破解雷同化的怪圈呢?我的总建议是推陈出新、兼容并包。具体而言:首先,文化活动是由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构成的,社区工作者往往对前者十分倾心,但今后更要重视营造精神层面的内涵。艺术和精神,性格分别为“动”和“静”,好比“浓抹”和“淡妆”;“动”过剩而“静”短缺,社区文化就很难上品位、上层次。所以,要提倡两个层面都有所倚重,正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其次,象联组学习那样实施相邻社区“联组活动”,尤其是在“唱唱跳跳”加“夕阳红”方面要进行联合,在联合中“合并同类项”,做到“去粗存精”、“取长补短”。这样,一方面可以刺激社团提升水准,另一方面也就可以扩大受众面。
第三,探索跨部门、跨行业的文化合作。对于社区文化而言,尤其是应注重和我区“四大”资源的精神层面共建。“十一五”期间,我区也重视“四大”资源;但主要是强调如何把她们的技术研发转为我区的“税源”。而“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把她们的精神财富转化为社区文化“活的源泉”。(作者系区政协委员、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文明办主任)